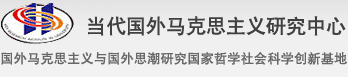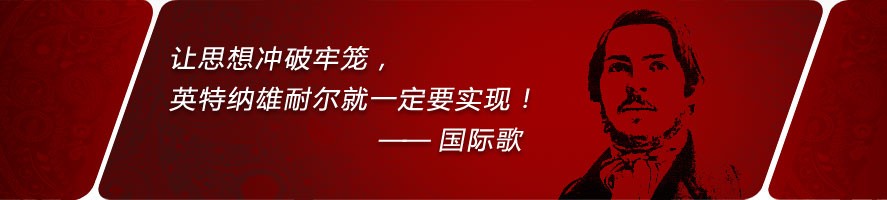2022年8月22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在线上成功开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老师主持了开班仪式,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双利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春明老师出席了本次开幕仪式。
在开幕仪式上,吴晓明教授首先发表了致辞。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肯定性的回顾后,吴晓明教授指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这突出体现为返回到马克思的学说这一理论基点以及对接当今现实问题的两大任务。孙向晨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哲学学院长期合作的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班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传统,本届暑期班的主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厚根基和开阔视野,并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能够扎根于中国大地。孙向晨教授对参加暑期班的成员表示欢迎,并祝暑期班取得圆满成功。张双利教授具体介绍了本届暑期班主题的两大特征:一是主题的相对集中,也即理论内容上集中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二是研究维度的多样,其中不仅包括了对经典社会理论的研究,还包括了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及超越这个理论框架的新的努力的研究。张双利教授还指出了暑期班的设立旨趣以及暑期班和博士生论坛的联动,鼓励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努力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走向深入。
专家报告(一):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开幕式后,吴晓明教授做了本次暑期班第一场专家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吴晓明教授指出,熊彼特和雷蒙·阿隆都曾指认了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地位,而研究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就是采取理论上的返回步伐,这使我们可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理论上的得失成败进行估价。比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基本定向,但其中“社会”的概念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体现在“总体性”概念被用于深入把握作为整体的社会。雷蒙·阿隆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中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二者研究的问题是一种学院中的“康德式问题”,也即更多地关注哲学的先天条件而不是社会历史实在。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理论工作。在报告中,吴晓明教授通过讨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理论渊源、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两重性以及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深入而全面地展现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根基地位。
首先,吴晓明教授探讨了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也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史无前例地将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原理引入到了哲学之中,要求一种理解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思辨总体”的立场,从而破除了被一般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采取的原子论和契约论的出发点——也即孤立的、非社会的个人。在《法哲学原理》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黑格尔把抽象法和主观法的本质性引入到伦理,也即包括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去。除此之外,黑格尔对表现为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以及单纯的“应当”的主观思想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这两点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一笔重要的遗产。同样,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之中,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对感性对象性概念的揭示,从高级直观上得到考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凸显出来,这成为了费尔巴哈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并使得费尔巴哈成为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者之一。吴晓明教授特别提示大家注意,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一点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次,吴晓明教授从性质方面讨论了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两重性,也即人类社会的概念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使用的社会概念指的是人类社会,其内涵包括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以及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一概念力图对现存社会进行否定,因此是批判的。与此相对,市民社会的概念是实证的、肯定的,要求通过政治经济学对既定社会的私有财产的运动进行研究。不过,吴晓明教授在对“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的观点进行分析之后指出,自我异化指的是市民社会的概念,异化的自我扬弃指的是人类社会的概念,二者是连成一体的,也即人类社会的展开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找到其理论和经验的基础,同样,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是以社会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的。就此而言,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建构缺一不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遗产,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以及费尔巴哈哲学中无法被弥合的高级直观和普通直观下两种社会概念的分离。
最后,吴晓明教授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核心定位在“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之上。就黑格尔的社会理论而言,社会的本质是被引导到国家的理念之中,并且最终又被引导到绝对之中的,其中活动着的主体是绝对精神。与此不同,马克思深入到了社会历史之本质性的一度中,使得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取代了绝对精神,成为一切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一既定的社会指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把握作为实在主体的既定社会,就需要作为辩证法的真正内涵和本性的具体化,这要求超出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而去把握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这样一来,普遍性就成为深入到实体性内容当中去的、有生命力的普遍性。就此而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以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环境为基准来实现具体化,这一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专家报告(二):涂尔干论“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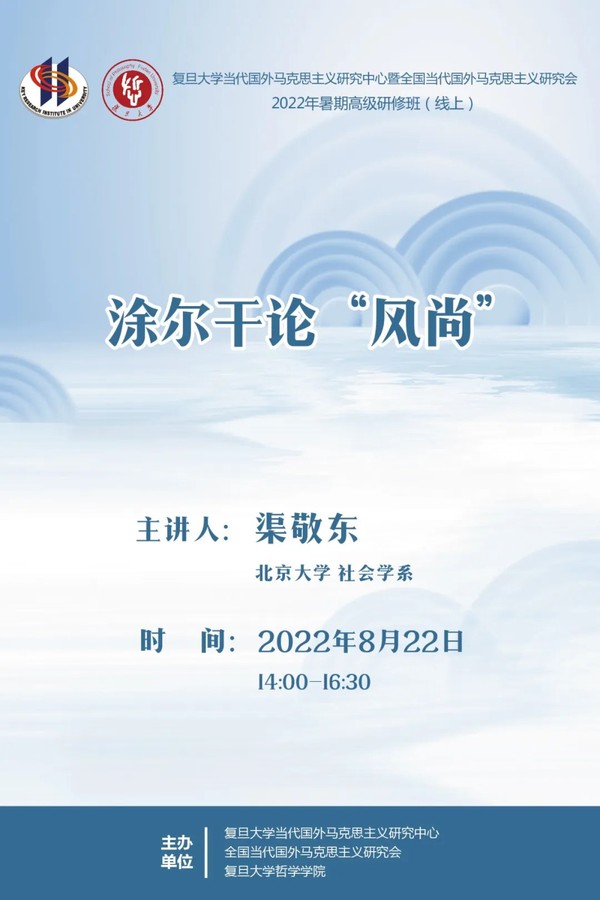
2022年8月22日下午14时,来自北京大学的渠敬东教授为暑期班学员作了题为“涂尔干论‘风尚’”的报告。讲座由张双利教授主持。
渠敬东教授以风尚(mœurs /mores)为切入点,不仅将涂尔干思想的基本框架清晰地呈现给听众,而且也以此为线索,梳理了理解现代社会的思想史脉络。讲座大致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风尚”这个概念入手,揭示近代启蒙哲学如何能够真正告别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时代,并开始去把握支撑起社会生活的根本维度:社会事实和集体意识;第二部分则聚焦于涂尔干自身,揭示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自我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恢复与整全社会的和谐关系?他已经看到,现代个体与整全社会之间的病态关系,已经发展成了两极对立,并进而引发了一次次社会灾难。带着这个问题意识,涂尔干展开对从历史文明的考察,他不仅仅回溯了历史环节,考察了原始宗教生活,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教化和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试图找到回应这一时代难题的道路。
和涂尔干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在二战后的探索,就是想要找到应对这一问题的可能线索: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家关注涂尔干对神圣性的讨论,他要以此来讨论在现代世界中,后世俗化的社会整合如何可能;为此,哈贝马斯必须要把涂尔干的神圣性非神圣化、语言化,将其转化为交往理性。对涂尔干教育研究的关注则代表着另一条道路,对个体性和社会性、世俗性和神圣性之和谐关系的塑造或恢复,落实在制度层面则要依靠职业法团,它既与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相关,又与社会生活的整全性、神圣根基相关,这是以霍耐特为代表的后哈贝马斯的理论家们的关切之一。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渠敬东教授就“风/风尚”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被拣选”展开了讨论。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来自王汎森先生的文章“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概念”。王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历史学家往往看重如何还原事实、用事实构造历史,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学问。与之对照,对“风”的关注则着眼于解释学理解,是去把握弥漫在特定社会中的、对其成员的人格和性情起到塑造作用的东西。中国人对“风”并不陌生,《诗经》中有风、雅、颂;《论语》也谈到君子小人和风的关系。在法国思想史中,类似的概念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就有了。伏尔泰的《风俗论》,标题中用的词就是复数形式的mœurs,这个词以道德为基本意向,指以教化产生的影响。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也是对mœurs进行讨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是对伏尔泰和卢梭论“风”的继承,他以科学化、体系化的方式讨论了这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法”并不是实证法学意义上的法,而是整个世界构造的基本原理或总的精神。从这些思想家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不再将对世界的理解置于纯粹神学或形而上学的维度了,对真理的把握要从“风”着手了。正是基于这一转变,孟德斯鸠认为,没有最好的政体,只有最合适的政体。他将政治划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本性(nature)着眼,也就是对政体结构的探讨,一般的讨论往往停留于此,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孟德斯鸠特别强调的本原(principle)维度,也就是风。只有当政体与风尚相匹配时,政治才可能是好的。亚当·斯密也明白风的重要性,他认为同情共感的模式比形而上学观念存在的所有设定都重要。同样的,相较于对政体结构的分析,马克思更看重结构化了的社会风尚——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者基础(infrastructure)。渠敬东教授指出,这是理解世界方式的一个根本变化,从存在、观念、神学出发的各种思想体系不再是最重要的,风尚成为马克思、涂尔干等思想家的科学的基础。
讲座的第二部分首先讨论了涂尔干的方法。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他说,要把握风和风尚的学问,核心在于把握作为“物”的社会事实。风并不是纯观念的东西,而是可以把握的社会物。道德统计学(moral statistics)是他用以把握此“物”的手段。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地域当中的人群,因为处于这一特定情境中,就会相应地处于特定的生活状态(如突然遭受天灾的某地居民)。这个特定的生活状态就是要把握的“物”或风尚。道德统计学要把握的不是个体的特殊状态,而是借着个体表现出来的、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社会情感。涂尔干将社会现象分为正常(normal)和反常(abnormal)两类,渠敬东教授指出,如果按照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来看,处于中间段的可以视为正常或凸显风尚的部分。大家对于一件事情在情感或行为反应上差不多,这样的情感或行为就被视为正常。在此渠敬东教授特别强调,这里不是要寻找观点或意识的差别,而是要抓住常人的一般反应以及塑造此种反应的底层结构。涂尔干的这个基本问题影响了整个20世纪所有重要思潮的发展。在语言学方面,索绪尔要探讨的就是在一个共同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人们使用语言的结构特征是什么;这里指的不是语法规则的特征,而是进入到生活世界里的规范特征。哈贝马斯普通语用学分析的基本思路就来自于此。就现象学来说,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意向性和意向对象,康德式的先验认知图式被在大多数人中发生的具有规范性的意向结构取代了。后结构主义则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反常,以期从中发现在正常中无法发现的真理。法兰克福学派也很重视反常,如《启蒙辩证法》对萨德的讨论、阿多诺对否定性的强调。
回到涂尔干,他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规范(normal)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就涉及到涂尔干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在渠敬东教授的叙述中,涂尔干对人的理解和对社会(世界)的理解是不能分割的,正是社会性的方面与个体性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个体。也就是说,个体并不是以纯粹个体的、原子的形式生存的,他一定已经是“风俗化”的个体。涂尔干继承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分,但是又超越了笛卡尔。按照他的观点,人在心灵的方面可以区分为(a)以个人感觉和激情为基础、扎根有机体之内的纯粹个体存在,和(b)以意识与理性为基础、纯粹非个体性的社会存在,后者包括社会累积的知识、传统习惯、既定社会条件等等;二者以记忆、想象和联想为纽带。从身体角度看,人有自己具有本能的自然躯体,社会也有自己的躯体,集体欢腾是社会有机体的实现状态,二者的纽带是仪式、仪轨;通过仪式、仪轨,个体被淹没在集体欢腾中,社会得到凸显。社会性的要素在这两方面渗透到个体当中去,参与到对个体的塑造过程。这是涂尔干研究的一个进展。前面提及涂尔干要把握作为物的社会事实,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进一步挖掘,他进展到了作为心的集体意识。(注意,从社会事实到集体意识的进展不对应本段心灵与身体二分)对这种“内部状态”的研究是涂尔干宗教研究的核心,因此教条释义学并不是他的关注重点,他真正关注的是宗教的社会构造。
涂尔干关注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扭曲:一方面,随着个体思维的发展,人们变得自我主义,产生了自我和社会规范的疏离;另一方面,抽象、普遍的观念越来越失去与具体生活的联系,人们特别容易形成纯粹的普遍意识,但同时失去了关于具体社会生活的思维。于是产生了自我分裂,既特别自我又容易被抽象口号俘获,由此引发了诸多问题。根据渠敬东教授的观点,社会生活的神圣性在这个时候已经丧失了——而从涂尔干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就在于不断侵蚀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存在于具体的生活世界当中,不能通过证明获得。因此,涂尔干必须进入到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去,必须去讨论具体情境下的社会关系、组织形态、风俗等等。通过回溯历史文明,涂尔干要探究神圣性,并进而理解规范(normal)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涂尔干的宗教研究。韦伯的宗教学研究是要从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各大文明的构成,讨论其文明结构;这是一个比较的视角,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历史是其核心问题。涂尔干关注的则是社会人之神圣性的基础,或者规范和社会的基础。其原始宗教研究旨在找到神圣存在的证明,是社会的本体论论证。图腾制度研究是对康德问题的转化,考察作为知识和范畴的思维图式——我们通过社会中已有的图式来认知这个世界。信仰体系与膜拜体系研究旨在探索社会实在的符号表征,即通过集体表现过程来表述一套真理或价值系统。乱伦禁忌研究着力于寻找道德生活和社会规范的起源,指明道德性不是我们通过反思的知识来超越自身,而是由给定的社会以神圣的方式灌注给我们的。总而言之,社会性的积淀以神圣性为中介参与到个体构造当中去。
涂尔干进一步将目光聚焦于教育,他的教育研究核心在于把信仰-价值、学术-教育、组织-学校、政治-帝国到现代国家统一在一起而形成真正的历史现实。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涂尔干指出,知识的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不同时代的风尚也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授的内容会有不同侧重。但无论如何,涂尔干相信,教育能够承担起协调神圣与世俗、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任务。渠敬东教授举例说,通过毕业典礼这一仪式,学生们学习的知识不再只意味着博得稻粮的手段,更意味着社会责任等等。
最后,渠敬东教授指出,风尚这一概念可以统摄涂尔干各个层面的思想,也可以用来把握启蒙以降的思想脉络,更可以用来把握历史文明。但一如王汎森先生注意到的,这个概念今天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缺乏“风尚”的视角。渠敬东教授勉励暑期班学员要拓宽眼界,纵深、横切、拉开距离地看历史、搞研究,要把握住时代的风尚和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