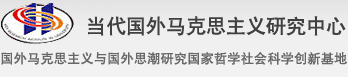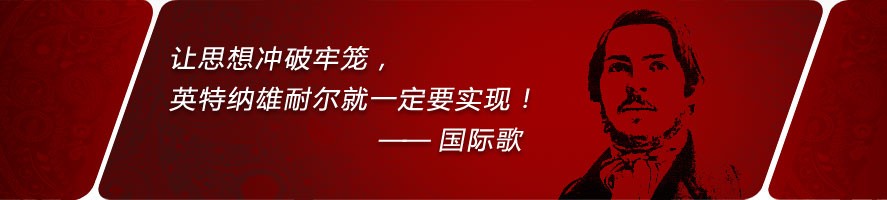2024年8月13日上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在复旦大学第六教学楼举办了第四场专家讲座,并于下午组织了第一次学员小组讨论。
专家报告(四)
海德格尔已经“动手”,
梅洛-庞蒂为什么还要“用眼”
——从现象学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联姻谈起
2024年8月13日上午,来自浙江大学的杨大春教授作了题为《海德格尔已经“动手”,梅洛-庞蒂为什么还要“用眼”——从现象学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联姻谈起》的报告,讲座由王春明副教授主持。
杨大春教授首先介绍了梅洛-庞蒂的一般背景,分别从梅洛-庞蒂本人思想史脉络和梅洛-庞蒂所处的现当代哲学流派归属对其思想进行了整体的把握,接着又对西方哲学主流传统中梅洛-庞蒂哲学所针对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杨大春教授认为,梅洛-庞蒂批判的对象主要是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接受的主要影响则来自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对于他要解决的问题来说,他更愿意接受的是来自黑格尔主义而不是康德主义的灵感。梅洛-庞蒂对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实际上将他自己的哲学纳入了现当代哲学的主流进程中:笛卡尔开启的现代性哲学问题一直延续到梅洛-庞蒂(以黑格尔为界限划分为早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性),梅洛-庞蒂晚期思想则开启了当代性。当代性是一个比后现代性更具积极意义的概念。后现代性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当代性则转向描述,它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转型下人的精神面貌。杨大春教授以如下哲学术语表达现当代哲学进程:早期现代哲学的主要形式是观念主义/唯心主义(Idealism),后期现代哲学主要表现为精神主义/唯灵主义(Spiritualism),当代哲学则归结为各种形式的物质主义/唯物主义(Materialism)。最后,杨大春教授在20世纪法国哲学进程中,以“柏格森/布伦茨威格——萨特/波伏瓦——列维-斯特劳斯/福柯”为主线对梅洛-庞蒂哲学思想的变化进行了梳理。
杨大春教授认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联姻正是在20世纪人道主义思潮下,通过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精神主义解读得以实现的。福柯把人之生定位在19世纪,认为人是19世纪的发明。其实,笛卡尔哲学早已做出回到人自身的努力,但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他仍然预设了上帝。这表明早期现代性仍然突出人的神性。法国哲学的3H时代,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实存主义(存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是人道主义的黄金时代。在福柯看来,人道主义是与黑格尔、马克思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只不过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思考20世纪而做出的充满魅力的、哀婉动人的努力。法国哲学与社会思潮联系紧密,马克思思想的广泛影响是通过社会运动表现出来的。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共命运。但是,以梅洛-庞蒂和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实存哲学注重1807年的黑格尔而不是1827年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而不是《法哲学原理》),所以法国哲学重视的黑格尔,是经过了精神主义解读的黑格尔。杨大春教授认为,梅洛-庞蒂的如下原话表明,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强调身心统一的,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对立:“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会用头走路,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它不会用脚来思考。毋宁说,我们既没有必要关心其‘头’,也没有必要关心其’脚’,我们关心其身体。对于一个学说的全部经济学的、心理学的说明都是正确的,因为思考者从来都从他自己之所是出发进行思考。”在梅洛-庞蒂,精神是代表了身心的统一。在康德那里,精神主要与人的静态的、逻辑的、结构性的先天认识形式联系在一起,而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则是辩证的、历史的和发生的,后者的看法很容易被梅洛-庞蒂转换成为自己的理论框架。法国现象学主要分为强调主体的实存论哲学和关注知识的概念论哲学两个流派。实存论哲学从海德格尔角度综合3H思想,同时赋予它们以精神主义色彩,以比朗的“我能”取代笛卡尔的“我思”,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从无身的转换成具身的,将海德格尔式不言明的身体指向阐发为彰显的,将胡塞尔的超然认识论解读为在世实存论。概念论哲学比较特别,如巴什拉《空间的诗学》《梦想的诗学》等作品充满诗意,带有很强的人文色彩,区别于英美哲学突出概念连续性和语言分析的倾向,但又与现象学主流的解释学倾向不同,这一流派走向福柯、德里达的解构论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杨大春教授指出梅洛-庞蒂很少引用海德格尔,但其思想相比于经常被引用的胡塞尔而言却是更加倾向海德格尔的,这种倾向体现在身心统一的理解上。胡塞尔的思想资源影响了诸多现象学家甚至是非现象学家,许多哲学家在胡塞尔这里找到了资源,并在新的框架中产生不同的思想分支。梅洛-庞蒂不断引用胡塞尔的资源,也经常提到胡塞尔的贡献,但他的哲学却明显地倾向海德格尔。如同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不引用马克思,梅洛-庞蒂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几乎很少提到海德格尔。福柯指出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早已全面渗透,因而无需引用,这样的思想谱系对梅洛-庞蒂也同样适用。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都是此在的形而上学,古代的哲学是实体形而上学,早期现代哲学是主体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批判主体形而上学,为我们提供的是此在形而上学。语言—身体—他者代表了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主要维度。主体在笛卡尔那里就是心灵。主体形而上学的解体首先意味着从身心二分到身心统一,身体获得了突出的强调。与此同时,以前的哲学是不关心语言的,因为语言仅仅是表达思想观念的工具。但是,到梅洛-庞蒂等人那里,语言已经不再能够清楚分明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开始变得结结巴巴,原因在于,思想不再是透明的,而是含混的,语言本身同样不再是完全透明的,它是半透明的,正因为如此,语言的自身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在哲学中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另外,无论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甚至在黑格尔那里,我与我们是可以画等号,他人不具有哲学地位。但在19世纪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开始变得明显,他者开始出现。无论如何,语言、身体和他者共同瓦解了主体形而上学,但用语言学转向不足以充分表达从早期现代哲学向后期现代哲学的演变。此在形而上学也表现为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并因此从强调“心”转向强调“身”:“心”意味着我思,“身”意味着我能,情感意志一定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身体是意志的直接的客观化。黑格尔的思想已经隐含了身体的重要性,这种对身体的强调并不是对身心关系的颠倒,而是一种身心统一。海德格尔哲学几乎不谈身体,甚至不谈意识也不谈精神,但“在手”、“上手”则是经常出现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概念。实践哲学突出的正是“动手”。事实上,“手”就是身体的表达,“手”代表着触摸、触觉。海德格尔哲学围绕在世界之中存在展开,这意味着他不再像苏格拉底一样悬在半空中超然旁“观”。这其实表明,海德格尔哲学是扎根的,其哲学是触觉中心论的而不是视觉中心论的。然而,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梅洛-庞蒂为什么还要用“眼”?甚至用“心”?梅洛-庞蒂始终强调的是“看世界”,尽管从“心”看转向了“眼”看,其著作中主要使用的都是与视觉相关的词语,甚至晚期的主要著作都围绕视觉展开。但这并不妨碍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都属于此在形而上学,因为他们都在用身体的某一部分来代指全体,却并不会局限于某个部分,即他们事实上强调的都是整体的身体图式。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批判性的,但梅洛-庞蒂的哲学却是包容性的,因而梅洛-庞蒂选择了用传统哲学经常涉及到的“看”来将以往的哲学吸纳进来。其实,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探讨触觉的内容也是很多的,关于左手与右手相互触摸,乃至我的手到他人之手的相互触摸的描述都是非常经典的。无论如何,梅洛-庞蒂既不认可经验论的原子主义知觉观,也不认同理智论的整体主义知觉观,他的知觉现象学突出了身体图式及其代表的全面意向性。
杨大春教授回到梅洛-庞蒂思想本身,梅洛-庞蒂为克服主客二分,从早期的身体图式过渡到后期“肉”的概念,始终围绕着身心统一原则展开。梅洛-庞蒂的早期哲学有着浓厚的认识论含义,但这种认识论是围绕身体主体展开的。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各个部位之间并不存在主要、次要的关系,而是互相协调、完整统一的。我们在塞尚的画中“看”到苹果的味道(“一幅画包含了景象的味道”)。艺术在其哲学思考中都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最初,他认为现象学与普鲁斯特、塞尚等文学艺术家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在后期,他表示当代哲学中包含着诗意的非哲学倾向。梅洛-庞蒂接受了身体主体与世界处于一种深层次的含混状态,在他看来科学实验的模式是套路化的,科学让我们与世界渐行渐远,艺术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就此而言,梅洛-庞蒂希望恢复我们对于现象场原初经验的知觉性的、艺术(感性)的感知。为了实现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综合,梅洛-庞蒂不像早期现代哲学家康德那样借助于自带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的意识主体的完全超然旁观的姿态,而是根据既具整体空间图式又有在世存在意愿的身体主体的保持适度距离的能力。有别于后期现代哲学家胡塞尔对无身的纯粹意识的迷恋,他拓展和深化了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操心结构的描述,强调入身的不纯粹意识。纯粹意识以心身二分为前提,不纯粹意识以身心统一为根据,意向性结构由此被改变了:意识意向性让位于身体意向性,主体的主动构造性从属于被动接受性。在其哲学中,梅洛-庞蒂围绕语言现象学展开,强调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文化形态都没有否定知觉的首要性。晚期的梅洛-庞蒂敏锐地洞察到,在我的身体内部、我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个体与社会、自然与文化之间,应该有某种原初的根基。他在前笛卡尔的哲学中,尤其是在希腊哲学中寻找灵感,发现了所谓的作为“元素”的“肉”,他寻求用“肉”这一概念来最终克服主客二分、意识哲学以及唯我论等难题。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神秘而野性的肉,不管野性的存在还是野性的精神都归属于野性的世界,身体之肉、语言之肉、历史之肉、世界之肉都是野性家族的成员。
讨论班(一)
2024年8月13日下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组织了第一次学员小组讨论。
本场小组讨论围绕着福柯与霍耐特的思想研究展开,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祁涛副教授和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副教授主持。讨论伊始,祁涛老师做了题为《米歇尔·福柯论批判理论》的发言,周爱民老师做了题为《霍耐特与法国思想界的对话》的发言。随后,学员们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踊跃的发言和积极的讨论。
撰写 | 王浩超
编辑 | 赵明哲
审核 | 吴一鸣
张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