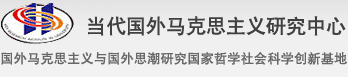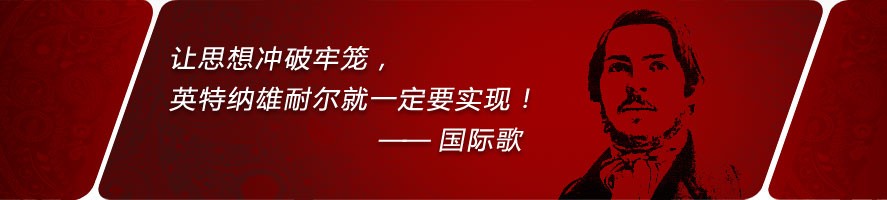哲学何谓?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哲学?用英语来表达,就是:What is philosophy? 在我看来,哲学研究者之所以要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哲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一切实证科学(如物理学、化学)比较,哲学缺乏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确定的研究领域。有的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生意义的探究,也有的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有的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语言上、逻辑上的分析运动,也有的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堪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实际上,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哲学家们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地反躬自问:What is philosophy? 以便在变化着的时代背景下对哲学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其二,正是通过对What is philosophy? 的解答,解答者选择了一种确定的哲学观,从而自觉地从这种哲学观出发去探索具体的哲学问题。如果一个研究者只注重对具体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却缺乏总体上的哲学观,他的思想就会始终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中,就像一个被打碎的花瓶,满地都是碎片。这样的研究者充其量只能成为哲学匠,却无缘升格为哲学家,更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哲学家。
其三,只有当研究者不断地追问What is philosophy?时,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新鲜的,即永不衰竭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在哲学研究中经常遭遇到的情景是:当某人站在哲学的殿堂之外时,总是充满好奇心地追问:What is philosophy? 而一旦成了哲学系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他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追问这个问题了,仿佛他研究哲学必须以忘记哲学作为代价。其实,这种不追问的状态正是哲学思维衰退乃至死亡的一个标志。下面,我们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索“哲学何谓”的问题。
哲学概念的来源
英语中的Philosophy,在希腊语中是φιλοσοφια,在拉丁语中是philosophia。如果其希腊名字拆开来:φιλο-是“热爱”的意思,-σοφια则是“智慧”的意思。因此,许多人把Philosophy理解为“爱智慧”(love of wisdom)。毋庸置疑,从事哲学研究(do philosophy)必定包含着对智慧的热爱,但“热爱”不过是一种情感。尽管哲学包含着对情感的研究,但在我看来,它不应该被归结为感情。哲学,就其最基本的表现方式来说,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索普遍性的问题。虽然对哲学概念所做的词源分析也是哲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但把这种方法用到对哲学自身的探索上似乎并不合适。正像一条河流的源头并不等于它的本质一样,φιλοσοφια这个词的来源也并不等于它的本质。在我看来,哲学不啻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且它本身就是智慧。显然,智慧(wisdom)与知识(knowledge)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果说,作为已然形成的观念,知识包含着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和已然死亡了的、僵化的东西,因而需要加以甄别的话,那么,智慧则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灵活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的和核心的意识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正是这种意识确保智慧永远不会变质,也永远不会僵化。
在对哲学的本质做出了上述阐释以后,接下去要追问的是:究竟是谁把西方人使用的philosophy译为汉语中的“哲学”?为什么“哲学”这个译名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哲学”中的“哲”字究竟是什么含义?让我们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解答。
众所周知,西方人称作philosophy的学问,在古代中国通常被称为“玄学”、“元学”、“理学”或“道学”。自明代以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道布教,他们既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技术和艺术,也带来了西方philosophy不同流派的思想。然而,当时的philosophy在中国的译名尚未取得统一,它曾被译为“理科”、“理学”、“性学”、“爱知学”、“性学”、“智学”和“格致学”等各种不同的名字。尽管这些译名在中国学术界流传一时,却从未得到过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据陈启伟先生在“哲学译名考”(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一文中的考证,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翻译上,日本学者西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70年,西周在其生前未发表的、由学生整理的讲演笔记《百学连环》中最早使用了“哲学”这个译名。1874年,“哲学”这个译名首次出现在西周公开出版的著作《百一新论》中。当时,这个译名也没有为日本哲学界所普遍接受,不少日本学者仍然以“理学”对译西方的philosophy。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在编撰日本第一部《哲学字汇》时采用了西周的“哲学”这一译法。从此,这一译名逐渐成为日本哲学界普遍接受的名称。
人们也许会奇怪,“哲”和“学”都是汉字,为什么日本学者西周要用汉字来译西方人的philosophy?因为从历史上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汉字是日本人使用的唯一文字,而现代日语就是由汉字和假名共同构成的。日本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经常用已有的汉字来造新词。明治维新时期,由于大量新思潮从欧美涌入日本,亟需用相应的译名把它们的含义准确地传达出来。于是,像西周这样的思想先驱便在传统的汉字的基础上造出了“哲学”这个新词。尽管在汉语中“哲”和“学”这两个字早已存在,但中国学者从未像西周那样把它们合成为一个新词。
众所周知,在《诗经》中有“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样的诗句,而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哲”是通晓事理、聪明睿智的意思。有趣的是,日本学者西周用中国字创制出来的译名“哲学”又返回中国,成了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对西方人的philosophy的定译。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哲,知(智)也。”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哲”,同“悊”或“喆”。甲骨文中无此字,金文作,小篆作。“哲”字上半部分为“折”。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折,断也,从斤断草。”“折”字在甲骨文中作,在金文中作,在小篆中作。“折”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相当于西方人说的“下判断”或“做决定”。显然,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睿智的人一定是善于果断地下判断的人。人所共知,在楚汉之争中,项羽后来之所以被困于垓下,在四面楚歌中自刎,因为他优柔寡断、缺乏决断。他的谋士范增曾批评他“有妇人之仁”,尤其是在鸿门宴上未对刘邦痛下杀手,以至于刘邦羽翼渐成,后来得以一统天下。其实,细心人一定会发现,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见解。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物,他整天纠结于to be or not to be(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对他面对的局面缺乏明确的判断和坚决的行动,从而酿成了悲剧。
如前所述,现在所用的“哲”字在金文中作,即“悊”,直到小篆中才嬗变为,即“哲”。如何看待“悊”字向“哲”字的演化?从一方面看,把隐藏在心中的判断通过嘴巴说出来,也就使判断明晰化、公开化了;从另一方面看,嘴巴上说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在心中经过反复思考而得出来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可能心中想的是一套,嘴巴上说出来的是另一套。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复兴似乎应该寄希望于从流于口头表述的“哲”重返注重心灵深思的“悊”,也就是说,使“哲学”复归为“悊学”。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主题上来。我们还需追问的是: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哲学”这个译名?据陈启伟先生的研究,中国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87)中谈到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时,曾经使用过“哲学”这个译名;蔡元培先生也是较早接受并引进“哲学”这一译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说自己“丁戊之间,乃治哲学”。所谓“丁戊之间”也就是1897-1898年间。毋庸置疑,在普及这个译名时,起了较大作用的是梁启超先生。他在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在那里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译介西方哲学的文章,使“哲学”这一译名很快成为报刊上的常用词,也成了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定译。
由上可知,中国人以“哲学”译philosophy,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一个突然的触动,当代中国学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哲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呢?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讲学,他有一个著名的见解是“中国没有哲学”。不难想象,这个见解甫一出笼,立即引起了一部分学者的抗议。随之,中国哲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大讨论。其实,只要人们注重对上下文的分析,就会发现,德里达并没有贬低乃至否定中国哲学,他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换言之,他的观点不过是肯定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当时,我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虚假而有意义问题》的论文,就上面提到的合法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关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假的问题。尽管与哲学这个译名对应的philosophy是西方人,尤其是古希腊人创制的一门学问;尽管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中国人对哲学的理解与西方人是有差异的,但决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哲学不具有合法性。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任何系统的文明都无例外地是由四大板块组成的。前面三个板块分别是:宗教(包括巫术)、实证科学、艺术。至于第四个板块,西方称为philosophy,而中国人在把“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定译之前,对第四板块有完全不同的称谓,如“玄学”、“元学”、“理学”、“道学”等等。这就启示我们,只要中国文明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着第四板块,用什么语词(即概念)去称谓它,完全与合法性无涉。打个比方,中国人用“水”这个用语称谓一种液体,而这同一种液体,英国人称作water,德国人称作Wasser,法国人称作eau。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对这种液体的称谓——“水”是不合法的吗?显然不能。要言之,任何文明只要包含着第四板块,怎么称呼它是一个完全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
有人也许会责问我:既然你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又说它是“有意义的问题”呢?因为当我说合法性问题是假问题时,是就第四板块在不同文明中拥有不同的称谓来说的,即不同的称谓与合法性无涉;而当我肯定合法性问题仍然有意义时,是就中国文明中的第四板块,即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成果的形式来说的。这里说的“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成果”是指当代中国出版的哲学方面的研究性论著,而这些论著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合法性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这些论著是否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如果不符合,当然就是不合法的。举例来说,假定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少得参考国际哲学界公认的30个权威性的文本,而刚在中国出版的某部研究著作只参考了其中15个文本。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这部著作在形式上是不合法的。第二个层面是:这些论著中关键词的含义是否得到了明晰的界定?假定某篇哲学论文有五个关键词,而这些词的含义都没有得到严格的界定,这篇论文怎么可能传达出明晰的观念呢?显然,这样的哲学论文也是不合法的。
当代中国出版的哲学论著之所以常常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正是上述两个层面的缺失所造成的。其历史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的数学和逻辑学自近代以来都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而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中国人又缺乏普遍的兴趣;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滞后,也使中国缺失欧洲自笛卡尔以来追求确定性(certainty)的传统,而辩证法思想的早熟又助长了对确定性的漠视。这样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有赖于对研究论著的形式上的合法性的追求。
对提问方式的反思
我们在前面肯定了在哲学研究中不断追问What is philosophy?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存在着严重的偏失,正是这种偏失导致了研究者对哲学的错误理解和阐释。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喜欢提问,但很少注意到自己的提问方式是否准确。举例来说,当某人走进咖啡馆,侍者通常会以如下的方式向他提问:Coffee or tea?(您要咖啡,还是要茶?)显然,这个侍者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提问方式有什么问题。其实,侍者的提问方式只有两个解:或者要咖啡,或者要茶。但如果某人既要咖啡又要茶,或既不要咖啡也不要茶,或他只要一杯牛奶等等。总之,他在需求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根本无法用Coffee or tea?这个问题去涵盖。由此可见,自然的、未经深思的提问方式常常会束缚解答者的思路,甚至把他的整个思路引向错误的轨道。
那么,What is philosophy? 的提问方式究竟有什么偏失呢?只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What is philosophy? 源自日常生活中的日葵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而What is this?的提问方式则蕴含着以下两个理论预设:其一,在以这种方式提问之前,提问的对象已然存在。比如,甲指着桌子上的一个杯子问乙:What is this?,乙回答道:This is a cup(这是一个杯子)。这一问答过程表明,在甲提出问题之前,作为提问对象的杯子已经摆放在桌子上。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杯子已经“在场”(presence)。因而当人们把What is this? 转换为What is philosophy?时,已经预设:哲学已经像那个杯子一样现成地摆放在那里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提问方式根本没有把哲学理解为一个生成过程。其二,What is this? 体现的是知识论语境中静观者的提问方式。当西方人教小孩学知识时,会指着某个对象问:What is this? 显然,这种提问方式关注的只是这个对象是什么,而全然不关心为什么这个被提问的对象(如杯子、哲学)会出现在这里?它与人类的生存活动究竟有何关联?要言之,这种提问方式遮蔽了被提问的对象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
既然源自What is this? 的What is philosophy?的提问方式存在着不妥之处,那么,如何以准确的方式提问呢?我们主张,通过建立“问题际性”(inter-questions)的方式,引入一个新问题来引导人们对What is philosophy?的解答。这个新问题是: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显然,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Why这个疑问词与What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对象本身,即它究竟是什么,而前者关注的则是对象与人类之间的意义关系,即它究竟为什么而存在。于是,我们建立了下面这个问题际性:“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一旦这两个问题被连字符号连接起来,它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第一个问题的引导下去回答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一问题际性使我们摆脱了传统的、静观的知识论对哲学本质的遮蔽,而是从哲学与人类生存活动的关联出发,对哲学做出了全新的理解,即哲学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究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学问。
基于上述理解,哲学意识本质上就是关于存在的意识。海德格尔的下述分析也印证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1942-1943)中,海氏指出,德语名词Bewusstsein(意识)是由词根Bewusst-(意识到的)和后缀–sein(存在)构成的。假如我们把词根与后缀的关系理解为动宾关系,那么Bewusstsein的构词法已经暗示我们,意识根本上就是对存在的意识。
哲学思维演化的四种方式
对哲学史的深入研究表明,人类的哲学思维演化至今,大致上经历了以下四种代表性的思维方式:
一是独断论(dogmatism)的方式思维
这是在康德哲学以前,尤其是在哲学发轫之初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无论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思维器官,还是人们使用的语言都是可靠的,个别事物乃至整个外部世界都是可以认识的。我们不妨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朴素的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思维方式流行时,它已经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挑战:一是早期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灾难频仍等,还无法准确地加以解释;二是巫术、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神秘说教,甚至在哲学家中间还广有市场;三是某些思维敏锐的哲学家已经对人的感觉器官、思维器官和语言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比如,古代智者派哲学家高尔吉亚曾经提出三点异议:“第一个是:无物存在;第二个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个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假如说,第一、第二条涉及对人类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可靠性的质疑,那么,第三条则涉及对语言的可靠性的质疑。显然,这种朴素的独断论思维方式无力回应上述严峻的挑战,它必然被新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二是现象论(phenomenalism)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与上述独断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认为自在之物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而前者则认为,尽管人们可以去思考自在之物,但它们是不可知的。这一由康德创立的现象论思维方式主张,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一种是现象,人们凭借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能够认识现象;另一种是自在之物,它们则是不可知的。在现象论思维方式的语境中,自在之物是由以下三个对象组成的,即主观上的最高统一体灵魂、客观上的最高统一体世界、主客观合一的最高统一体上帝。尽管在人们的感觉经验所触及的范围内并不存在自在之物,但为便于理解起见,我们不妨做如下的类比。假设李四这个人是自在之物,张三与他接触五分钟后便断言:“李四是个好人。”显而易见,张三的断言是错误的,因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可能做的断言是:“李四留在我脑中的印象是好的。”后一个断言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它只是对现象——李四留在张三脑中的印象的好坏做出断言,而不是对自在之物——李四本人的好坏做出断言。这种现象论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从不试图像独断论思维方式那样去认识自在之物,而是把认识局限在自在之物刺激感官时产生的现象上。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出人类的谦恭态度,但它留下的最大疑问是: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正如德国哲学家耶柯比所评论的,由于对自在之物的兴趣,人们走进了康德哲学,但是,也正是由于对自在之物的疑问,人们又必定会走出康德哲学。
尽管现象论思维方式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自在之物的谜语又促使人类超越了现象论的思维方式。
三是生存论(existentialism)的思维方式
为了探寻自在之物的谜底,叔本华做了如下的比喻:在一个化妆舞会上,康德为了找一个舞伴而求助于一位女性。他们在跳舞时配合得相当默契。舞会结束后,那位女性摘下了假面具。康德突然发现,那位女性正是自己的妻子。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康德从未结过婚。叔本华只是借助于这个假想的意象来表明,康德的自在之物非但不是不可知的对象,相反,正是他最熟悉的对象。那么,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呢?叔本华告诉我们,自在之物就是意志,而意志乃是世界的本质,它在人的生命、身体和欲望中得到了最贴近的、最充分的体现。这样一来,叔本华把在康德那里停留在遥远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重新带回到人间。
肇始于叔本华的生存论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颠倒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和认识是第一性的,意志和欲望则第二性的。叔本华把这个公案彻底地颠倒过来了。他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和欲望是第一性的,理性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换言之,意志和欲望是主人,理性和认识则是奴仆。理性和认识从来不会任意地去思索一个对象,它们思索的永远是自己的意志和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即使理性和认识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也永远是围绕着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而展开的。
生存论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是,揭示了人类思维的永恒的秘密,即思维始终是围绕着意志和欲望而向外伸展的。乍看起来,思维就像一架竹制的风筝,在无限广阔的天际翱翔、颉颃,它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的肚子上系着一条绳索,这条绳索就是意志和欲望。在叔本华之后,尼采、海德格尔等进一步改造并提升了这种思维方式,使之在当代精神生活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与其他思维方式一样,它也必须借助语言而被表达出来。只要人们对语言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还不甚了了,那么生存论思维方式不但不可能通过语言充分地彰显出来,还可能处于被语言遮蔽的状态中。
四是以语言哲学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因为不明了语言的性质而被纠缠在假问题中,就像苍蝇飞进了捕蝇瓶,无法挣脱出来。在维氏看来,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治疗性的,它不过是语言上、逻辑上的分析运动而已。通过分析,澄清语言问题,从而为误入捕蝇瓶的苍蝇们指出一条逃生之路。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形而上学、哲学连同当代语言已经遗忘、甚至完全遮蔽了存在的真理,因而形而上学和哲学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处于被终结的状态中,而由海氏唤醒的、取代它们的“思”(Deken)则开始了,思的根本任务乃是思存在的真理:“语言是存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个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沟还更不显眼。”在海氏看来,只有通过思把探寻存在意义的基本语词(概念)犁入到语言中去,语言才可能真正成为“存在之寓所”。
具体说来,这种以语言哲学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语义学(semantics)的方向,主要探讨语词、句子、文本、语境、互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指称(能指、所指)、意义、语义悖论之间的关系;探讨理想语言与日常语言、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的关系等等。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索绪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奎恩、戴维森、普特南、达米特等哲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是“语用学”(pragmatics)的方向,主要探讨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商谈的规则,涉及到商谈各方的语言资质(对语言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领会性以及表达上的真诚性的把握)、对共识的认可和明晰化;也涉及到对言语行为或以言行事问题的探索。如果说,哈贝马斯建立了普遍语用学和商谈伦理学,那么,奥斯汀、塞尔等人则就“以言行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上面,我们对哲学史上出现的四种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做了简要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人的思维大致上还停留在独断论思维方式的框架内,只有少数人的思维进入了第二、第三和第四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在第四种思维方式中,目前仍在英美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应该把分析哲学与分析哲学所蕴含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区分开来,我们主要借鉴的是分析的方法。事实上,只有自觉地适应这种语言学的转向,当代中国哲学家才能与国际哲学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当代中国哲学才能在新的对话和融合中创造新的辉煌。
(本文为原载《文汇报》201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