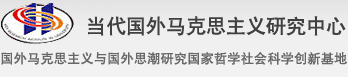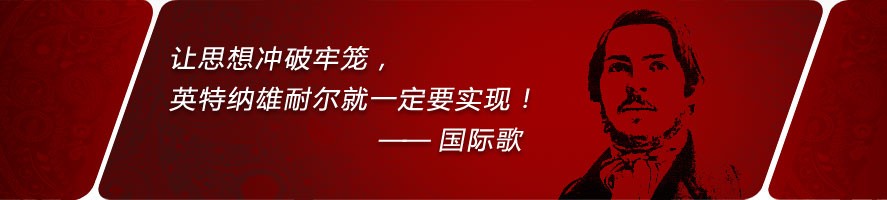在海德格尔那里,“思”与“诗”不可分,诗是他阐发哲学和神学思想的重要方式。海德格尔的这一思路使我想起中国古已有之的通过诗阐发存在关怀和人文意境的方式。的确,真正打动人心的诗歌与人切身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而真正启迪人心的诗歌无不深含高尚的人文意蕴。中国是诗的泱泱大国,在诗经、楚辞和唐宋诗词等作品中,不仅达到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峰,而且还抒发了体悟生存意义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崇高的人文精神。在当今时代,形而上学日益式微;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建构价值体系基础的做法越来越走不通。此时,我们追踪思想的源头,在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诗中,我们窥见建构别具一格的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希望。
关键词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中文诗愁生存体验人文意蕴
Existential Care and Humane Implication in Chinese Poems in Comparison with Heidegger’s Perspective about Poetry and Thought
Zhang Qingxi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eidegger thinking and poetry cannot be separated, and the elucidation of poetry is an important pattern for him to express h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is approach reminds me that poetry used to express existential care and humane impl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Indeed, the poems of deeply moving human’s hear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u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poems of really inspiring people often contain lofty sentiment. China is a country rich in poems, which demonstrated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Tang and Song poetry. They achieve not only unparalleled artistic peak, but also communicate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lofty humane spirit by their insight into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In this era metaphysics has declined, and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value systems with aid of metaphysics is already dead. In this situation, we glimpse a hope to nourish humanist spirit with unique Chinese style by means of tracing our cultural source and interpreting of the poems which are full of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Keywords: Heidegger, Holderlin, Chinese poetry, anxiety,existential experience, religious mood
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不可分,诠释诗是他阐发其哲学思想和神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后期的作品更是与荷尔德林等人的精妙诗歌诗结下不解之缘。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的前言中,他刻画这位诗人的诗歌“就像一个失去神庙的圣龛,里面保藏诗意创作物。”[1]在他晚年与《明镜》杂志的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的思想和荷尔德林的诗歌处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中。……我认为荷尔德林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指向未来,他期待上帝,因而他不能只不过是文学史思想中的荷尔德林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2]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中要找的是一个在神庙坍塌的时代中依然闪烁神圣精神的“圣龛”,是“期待”中的“上帝”。
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存在哲学。这种存在哲学是如何通过诗与“神”联系起来的呢?这是因为生存体验与神圣体验的关系。相对于这种体验,概念文字黯然失色,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南辕北撤。诗歌在此却神采奕奕,得心应手。的确,真正打动人心的诗歌与人切身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而真正启迪人心的诗歌无不深含崇高的意蕴。
海德格尔的这一思路使我想中国古已有之的通过诗阐发存在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方式。中国是诗的泱泱大国,在诗经、楚辞和唐宋诗词等作品中,不仅达到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峰,而且还抒发了体悟生存意义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崇高人文精神。在当今时代,形而上学日益式微;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建构价值体系的道路越来越走不通。此时,我们追踪思想的源头,在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诗中,我们窥见建设和激发别具一格的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希望。
“诗”与“愁”——“愁”与“存在”和“时间”
在中国古代,诗人被称为“骚客”,而“骚”的意思就是“愁”。诗人指感受敏锐、多愁善感、忧国忧民的人。《离骚》是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对于“离骚”这两个字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的话解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还指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在中文中,“忧”和“愁”是同义的。按照《说文解字》,“忧,愁也;”“愁,忧也。”这两个字可以连用,即“忧愁”。这样,忧愁就与中国诗词结下不解之缘。
“忧愁”是中文诗词经久不息的主题。“忧愁”是中文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这甚至可以从许多中小学生都会背诵的一首辛弃疾的词看出: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赋诗词,需要说愁。“愁”是诗的一个恒久的主题。“诗”与“愁”就像生命中的身体和灵魂一样密不可分。不知道愁,就写不出好诗,这连少年都知道。然而,少年没能真正体验到愁,所以只能“强作愁”。少年的人生经历有限,少年在家长的关照之下生活,还不用事事为生存操心。成年人就不同了,成年人经历过人世艰辛,想不愁也难了。
“愁”有时间维度,而时间是在生存中展开的。体验到生存,也就体验到愁。正如南宋词人吴文英所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把生存的境遇描写出来了,也就等于把“愁”描写出来了。一个人诉说自己的忧愁并不能摆脱自己的忧愁,因为只要生存就会有忧愁。诉说忧愁或许能宣泄自己的情绪,但忧愁的根源仍然存在。所以,当辛弃疾“识尽愁滋味”后,“欲说还休”。但不直接说“愁”,而把“愁”的生存境遇描写出来,却更能表达愁的真谛。中文字“愁”上面是“秋”,下面是“心”,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愁的意识活动和生存境遇。“秋”是一个季节,具有时间性质。在秋天,一方面禾谷熟了,人们在丰收后燃火庆贺,另一方面又在担忧即将到来的严冬。——储备的粮食是否够了?御寒衣是否准备了?辛弃疾只用一句“却道天凉好个秋”,就把那些使人发愁的生存境遇和人的愁的心理活动活龙活现地描绘出来了。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引述了一则罗马寓言:从前有一次,忧愁(cura)女神在渡河之际看见一片粘土,她动手把它塑造成型;这时朱庇特神走来,给它吹了一口气,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他们为其命名之事争执起来时,农神过来裁决:你,朱庇特,既然你提供了灵魂,你该在他死时得到他的灵魂;既然你土地神,给了他身躯,他的身躯在他死后就复归为土;而忧愁女神最先造出了他,那么只要他活着,“忧愁”就占有他。至于大家所争执的他的名称,就叫他‘homo’吧,因为他是由humus[泥土]造成的。在这个故事中,海德格尔所注重的不是“泥土”和“灵魂”这两种人的生前所来、死后所归的质料,而是人的在世存在的源头和基本方式“忧愁”和“时间”:“只要这一存在者‘在世’,它就离不开这一源头,而是由这一源头保持、确定和始终统治着的。‘在世’的存在,就存在而言,刻有‘烦’(忧愁)的印记。这一存在者的命名(homo)不是着眼于它的存在,而是就组成它的东西(humus)而言的。至于这一构形的‘源始’存在应在何处得而见之,则是由农神即‘时间’来判定的。在这一寓言中表达出了对人的本质的前存在论的规定;从上面的提法可以看出,这一本质规定一开头收入眼帘的那种存在方式就是始终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时间性变化的那一存在方式。”[3]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农神是主管季节和农作物收成的神,因此农神也是时间之神。中文字“秋”兼具季节和农作物收成的含义,而中文字“愁”兼具季节和忧心忡忡的含义,简直把“农神”和“忧愁女神”合二为一了。由此可见中国先人造字的精妙。如果说海德格尔为思考哲学问题乐于玩味希腊词的话,我们中国人更应琢磨中文字的深意了——它们是在中国人的生存语境中产生出来的。
对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Sorge”,在中国有多种译法。早先,陈嘉映沿用熊伟的译法,把它译为“烦”。我想熊伟把“Sorge”译为“烦”,很可能考虑到佛教中有关烦恼(梵语klesa)不离生活,生活即烦恼的看法[4]。后来陈嘉映在《存在与时间》的修订版中把“Sorge”译为“操心”,通俗了一些,易于大众理解。张祥龙主张把“Sorge”译为“挂虑”,自有他的一番道理。我更喜欢把它译为“忧愁”,因为“忧愁”不仅具有“操心”或“牵挂”的含义,而且更突出了时间的维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德汉词典》中,把“Sorge”译为“忧虑”、“担忧”,可见把“Sorge”译为“忧愁”,还是贴近该词的原意的。
海德格尔谈到“忧愁”的时候,区分了两种现身情态:一种是对具体的东西发愁,另一种是对存在本身发愁。前者表现为“怕”(“担心”)(Furcht),即对世内能够确定的有害之事的怕(担心),它可以通过具体的操劳活动排解。后者表现为“畏”(忧虑)(Angst),它是永远不能排解的,因为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5]在中国的古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忧愁的这两种情况的体验。后者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但是这种忧愁是无法销除的,所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对在世本身的忧愁是一种万古愁,是一种只要人在世存在,就会感觉到的愁,是一种无可名状、永远悬挂着的“忧虑”。
“忧愁”具有时间的维度。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谈到时间可以通过对过去的事情的回忆、对现在的状况的感知,和对将来的事情的展望表现出来。有关这一点,我想中国诗人也知道得很清楚。在以上所引证的辛弃疾的诗词中,他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充满童趣、爱上高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往事,感知到他如今识尽愁滋味的现状,察知秋凉,预感冬寒,为此担忧。通过“忧愁”把现在、过去和将来串联起来。“忧愁”是对生存状况的幽思,具有生存论的意义。
海德格尔企图通过忧愁揭示此在的基本结构。按照他的看法,此在(Dasein)不免一方面处于“被抛”(Geworfenheit)状况中,另一方面在进行“筹划”(Entwurf)。这是说,人生总要被带入到一种境域中,遭受各种忧患,接受各种挑战,从而进行筹划,试图解除忧患,改善其处境。“忧愁”就是在这种处境中产生出来的。人的生存论处境决定人势必忧愁,而人又经由忧愁改善其生存处境,发展自己。说来也巧,人的这种因“被抛”和“筹划”而“忧愁”的生存论关系也在“离骚”这个词语中表现出来。东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由此看来,“离”同时具有“遭遇”和“离别”两层含义:遭遇忧患,而进行筹划离别忧患,所以“忧愁幽思”,创作了《离骚》的伟大诗篇。
“客”与“回归故乡”
“客”和“故乡”是中国诗词中一对关键词。因为客居他乡,所以愁思回归故乡。“客”与“故乡”是人的生存境域;离乡背井和回归故乡是人生存中势必要发生的事情。人的存在就是一方面要离开他原先的居所,另一方面又要回归他原先的居所,人生处在一种旅途中。正如“忧愁”要通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概念来展开一样,“忧愁”也通过“客”、“旅途”和“故乡”的空间概念来展开。“客”、“旅途”与“故乡”成了刻画人的存在一组象征符号。正因为这个道理,当我们阅读到诗词中有关“客”、“旅途”和“故乡”的诗句时,总是被深深打动,感慨万千。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七绝之所以魅力无限,正在于它生动地刻画了人生旅途中的孤寂忧愁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当看到月亮已落下,听到乌鸦不停啼叫,会感到秋霜满天的凄凉呢?为什么在江边枫树映衬着船上渔火点点的美景中,独自发愁,难以入眠呢?因为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告诉他:你身是客,坐在客船上,来到异乡。每当我们处在人生旅途上的时候,从外出旅游、出差办事,到上山下乡,出国求学和打工,随着远离故乡的路程,异乡感的加重,忧愁就会加深。记得小的时候,背诵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没有什么感觉,但在一次久居国外的春节背诵它的时候,就黯然神伤,不禁泪下。
海德格尔喜欢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写了一首与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相类似的诗:
他的茅屋前的阴影里平静地坐着
犁田者,他的炉灶为这知足者升起炊烟。
和平的村庄里的晚钟
好客地为此旅人鸣响。
现在船只自然地进入港口,
远方城市市场上繁忙的喧嚣
快活地消失;无声的叶簇间
友朋聚餐的器皿闪亮。
我该去何方?会死者活着
靠报酬和劳动,劳逸交替中
万物欢乐;为什么惟独
我心中的刺永不入眠?[6]
这里也有“晚钟”,也有“客船”;“茅屋前的阴影”和“炉灶升起的炊烟”和可以对上“月落”和“乌啼”;“无声的叶簇”可以对上“江枫”;“器皿闪亮”可以对上“渔火”;“心中的刺永不入眠”可以对上“对愁眠”。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都在一个静夜来到“异乡”。他们为什么欢乐不起来呢?为什么要发愁呢?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客”,想回归“故乡”。如果说者两首诗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张继的这首诗刻意描写江南的美景,由此突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样的美景中游子还感忧愁呢?荷尔德林的这首诗刻意描写他乡的好客,朋友聚餐相会,以及靠劳动报酬生活,在劳逸交替中寻求欢乐,是在什么地方都会发生和大家都向往的寻常事情,由此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心中的“刺”依然永不入眠呢?既然我们为寻求美景来到他乡,既然我们为寻求美好的生活来到他乡,既然人生总是在旅途中,为什么我们仍然不知足呢?为什么我们还为思念故乡不能入眠呢?这个故乡究竟在哪里?这个愁究竟为何而生?诗人把读者引到这样的意境中去,对于这样的问题就让读者自己去寻求解答了。
“返乡”的宗教和哲学的意蕴
“故乡”、“客”、“返乡”是宗教中常见的隐喻,从“故乡”到“客”,再到“返乡”是世界各大宗教中的诸多宗教叙事的展开方式。基督教神学就是从《圣经·创世记》中“伊甸园”的故事开始的。伊甸园就是人类的故乡,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的照管下在那里过着幸福生活;后来他们由于受了“蛇”的诱惑,违背上帝的禁令,偷吃“禁果”,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成为“异乡人”,从此过着痛苦的生活;人类向往回归“伊甸园”,向往回归“故乡”。在这里,作为人类故乡的“伊甸园”是一个隐喻。人类被赶出伊甸园,沦为“异乡人”,也是一个隐喻。那么人类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呢?“异乡人”究竟意味什么呢?“异乡人”究竟怎样才能返乡呢?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以弗所书2.13)。……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2.19)由此看来,异乡人(外人、客旅)就是远离神的人,而回归故乡就是回归神的家园,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对于“远离神的人”,保罗所做的解释是离开神所赐予的生命的人,是受私欲迷惑,心思迷惑、心地刚硬的人。对于成为“神家里的人”,保罗的解释是被圣灵所感,与神和好,与神合一,居住在圣灵的居所内。这在道德上表现为“一切苛刻、恼怒、暴戾、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31-32)这一回归靠人自身不行,完全是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完成的。
西方哲学传统中很重要的“异化”(Entfremdung,alienation)概念很可能是从宗教传统中来的。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把希腊文“?λλοτριο?ν”翻译为“entfremden”。《新约·以弗所书》中有如下一段话:“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以弗所4:18)。在马丁·路德的《圣经》德文译本中这段话为:“deren Verstand verfinstert ist, und die entfremdet sind von dem Leben, das aus Gott ist, durch die Unwissenheit, so in ihnen ist, durch die Blindheit ihres Herzens”(Eph. 4, 18)。我们用哲学术语来翻译它,就成为:“他们的知性昏昧,异化于神所赐的生命,都因他们内中的无知,心眼瞎了。”我在此不是说应把“隔离”翻译为“异化”,而是想表明哲学中的“异化”的概念与宗教中的“隔离”的概念的关系。在基督教中,与上帝所赐予的生命的隔离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是罪恶,是苦难;回归上帝所赐予的生命是回归正道,是获得拯救,是幸福。德文词“Entfremdung”含有“疏离”、“隔离”、“陌生化”、“异化”等多层含义。它不但描述一种背离(家乡、共同体、本源、本性)而变得陌生化,变为他者的过程,而且还含有一种价值判断,即应该回归正道,回归故乡,回归自己的本源。
神学大都采取以哲学论证的方式来解释宗教的意境。与古希腊哲学相结合的基督教神学增添了对圣经中有关“异化”的叙事故事的解说方式。柏拉图主义的神学把神的国度解释为精神性的天国,把“异化”解释为灵魂从精神性的天国沦入到物质的大地上,束缚于肉欲的身体,而获得拯救就是灵魂从物质的牢笼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其原来的精神性的家园中去。海德格尔的哲学以“存在”和“存在者”取代了“精神”和“物质”,把“异化”解释为对存在的遗忘,即人沉迷于存在者(Seiendes)而不知其本源是存在(Sein)本身。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的诗的探讨就着眼于反对柏拉图式的异化论,揭示一切存在者真正的本源是存在本身,那里才是人的存在(此在)的真正的故乡。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这是特拉克尔诗中的名句。海德格尔发现:“这句诗让我们觉得突然置身于一个流俗的观念之中。依照这种观念,大地乃是稍纵即逝的尘世的东西;反之,灵魂则是永恒的、超凡的。自柏拉图学说产生以来,灵魂就被归于超感性的领地内。倘若灵魂出现在感性领域,那它不过是往那儿堕落了。这里的‘大地上’与灵魂是不合拍的。灵魂不属于大地。灵魂在此是‘异乡者’(ein Fremdes)。身躯乃是灵魂的囚笼——姑且这样说罢。在柏拉图看来,感性领域是非真实存在者,不过是行尸走肉。因此,灵魂显然只有赶快离开感性领地,别无出路。”[7]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流俗的见解是不对的。按照他的看法,灵魂不能离弃大地,灵魂只有在大地中展开自己才能获得生机。大地是灵魂的栖居之所。如果我们把灵魂视为“此在”(Dasein),那么它就要在生存的境域(Horizont)中展开自己。灵魂在生存中探寻,在探寻中领悟存在的真谛,从而获得拯救。“灵魂之本质在于:在漫游中寻找大地,以便在大地上诗意地筑造和栖居,并因之得以拯救大地之为大地。”[8]
那么灵魂为什么成了大地上的异乡者呢?因为灵魂发生了异化。灵魂不是从一个永恒的精神王国来到无常的大地上而发生异化,是灵魂受到物的引诱,执着于凝固已然的东西,遮蔽了自己而发生了异化。灵魂在存在者中寻找本源,忘了自己本身是一种“能在”,忘了在自己的展开之中体验存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最本己的能在对此在隐而不露。沉沦在世是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同时也是异化着的。”[9]
正因为灵魂异化了,所以“灵魂遭遇到了某种与之格格不入的、从而是奇异的事情,即它在大地上既找不到藏身之所,也得不到同情的回响。”[10]
噢,多么宁静的行进,顺着蓝色的河流
思索着那被忘却的,此刻,茵绿丛中
画眉鸟召唤着异乡者走向没落。[11]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几行诗在描述灵魂“在安宁和沉默中没落”。海德格尔做出这样的解释是不奇怪的。他在《存在与时间》中说过:“一般人自以为培育着而且过着完满真实的‘生活’”;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从这种安定情绪看,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一切大门都敞开着。沉沦在世对自己本身是起引诱作用同时也起安定作用的。……起引诱作用的安定加深了沉沦。”[12] 海德格尔在特拉克尔诗中听到知音了。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沉沦,意识到异化呢?这需要在灵魂的忧郁、痛苦之中反省观看:
你的火焰赋予精神以炽热的忧郁;
哦,痛苦,你是伟大的灵魂的燃烧的观看!
活着是如此痛苦的善和真;
一块古老的石头轻柔地触摸着你:
真的!我将永远伴随你们。
哦,嘴!颤抖着透过白杨树的嘴。
忧愁是此在生存的基本方式。诗人通过忧愁倾诉衷肠!哲人通过忧愁探究存在的真谛!圣人通过忧愁召唤人回归存在的故乡!觉悟的异乡者通过忧愁聆听存在的言说。这里,“颤抖着透过白杨树的嘴”象征存在本身在言说,暗示你要聆听存在的言说,而“轻柔地触摸着你”的“一块古老的石头”会使人联想起“存在”,因为在德语中“石头”(Stein)与存在(Sein)只差一个字母“t”,同时“石头”也有“墓碑”的意思,想到死亡会激发你领悟存在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看海德格尔如何解读荷尔德林的一首《返乡》的诗。上升到宗教意境,“返乡”就是要回归神圣的本源。海德格尔在这首诗中,看到的真是对这种神圣本源的探寻。海德格尔阐述,这首诗描写的是荷尔德林的一次返乡的旅程:1801年春天,作为家庭教师的荷尔德林从康斯坦茨旁边的图尔高镇,经由博登湖,回到他的故乡施瓦本。海德格尔发问:按此情景说,《返乡》该是描写一次快乐回乡,可是,这首诗的基调是“忧心”,它根本没有透露出这位返回家乡的人的欢快情调。这是为何缘故呢?是故乡的人对这位返乡游子的不友好?不是的。该诗分明写道:
一切都显得亲切熟悉,连那匆忙而过的问候
也仿佛游人的问候,每一张面孔都显露亲近。[13]
那么,这位诗人为什么如此忧心忡忡呢?这是因为荷尔德林把返乡当作一次对神圣本源的追寻,他希望在故乡发现它,但它依然隐匿着。当他抵达故乡之时,他的这种失望心情由两段诗句衬托出来:
一方面:
你梦寐以求的近在咫尺,已经与你照面。
另一方面:
但那最美好的,在神圣和平彩虹下的发现物,
却已经对少年们和老人们隐匿起来。
为什么神圣本源对“少年们”和“老人们”隐匿起来呢?因为“少年们”还没有离乡背井的经历,还没有回到家乡探寻本源的渴望。不见滚滚江河奔腾入海,不会激起探寻其源头的强烈愿望。“为此,向源泉的行进首先必须离开源泉。向源泉的行进并不是径直向着源泉行进。家乡的本源其实是什么,这在青年在家的成长之初恰恰是不能经验到的。”[14]而“老人们”则对大地上的“纯粹法则”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他们不再想去追寻那周而复始的法则背后的奥秘。但这奥秘依然吸引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这种人有着深切的人生体验而又不像“常人”那样流于习俗;他们能够在平常中看到不平常,在荒瘠中发现宝藏,在“自然”中看到“神圣”。荷尔德林认为,神圣者就是自然之本质。用他的诗句来说:
而从天穹高处直抵幽幽深渊
遵循牢不可破的法则,一如既往地
自然源出于神圣的混沌,
重新感受澎湃激情,那创造一切者。”[15]
神圣本源向勇于探寻者洞开门牖,而真正的诗人就是这样的探寻者和召唤者。荷尔德林这样歌唱:
我曾从伟大的天父那里听来许多,
我对他沉默已久,他高居云端,
不断更新漂泊不定的时代,主宰着山峦群峰,
他就要恩赐我们天国的礼物,召唤[16]
然而,诗人依然忧心忡忡:
歌者的灵魂必得常常承受,这般忧心,
不论他是否乐意,而他人却忧心全无。
为什么诗人不得不承受这种忧心的命运呢?因为:
我们不得不常常沉默;神圣的名字付诸阙如,
心儿在跳,言语却迟迟难发?[17]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神之‘缺失’是‘神圣的名字’付诸阙如的原因。”诗人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神缺失的年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寻觅“隐匿的发现物”。“因此,对诗人的忧心来说,要紧的只有一点:对无神状态这个表面现象毫无畏惧,而总是临近于神之缺失,并且在准备好的与这种缺失的切近中耐心期待,直到那命名高空之物的原初词语从这种与缺失之神的切近中被允诺出来。”[18]
“道”在语言的“破碎处”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通过语言显示自己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是人们又因为语言而遗忘存在,人们执着于言词只见存在者,不见存在。海德格尔写道:“我曾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语言乃是在场之庇护(Hut des Anwesens),因为在场之显露已然委诸道说之成道着的显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成道的方式。”[19]
这里涉及在场的东西和不在场的东西的关系。我们通常把在场的东西当作存有者,把不在场的东西当作尚未出现的存有者。但让我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把不在场的东西转变为在场的东西。把一切不在场的东西转变为在场的东西的真正的本源乃是存在本身。存在可以说永远既在场又不在场:说其在场,因为没有一个存在者不是藉着“它”而在场的;说其不在场,因为它永远无“象”。我们的语言符号是借助于形象而命名的,因此我们通常使用的名词都是用来命名存有者的。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本身是无名的。如果我们硬要按照名词指称对象的关系去理解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把存在误解为存在者。但我们把握了在场和不在场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语言的字里行间,在作为一条道路的语言的走向中领悟存在或领悟“道”。海德格尔写道:“语言之本质因素乃是作为道示(Zeige)的道说(Sage)。道示之显示并不建基于无论何种符号,相反,一切符号皆源出于某种显示;在此种显示的领域中并且为了显示之目的,符号才可能是符号。”[20]“通向说的道路在语言本身中成其本质。通向说(Sprechen)意义上的语言道路是作为道说(Sage)的语言。因此,语言的固有特性隐蔽在道路中,而道说作为道路让顺从道说的听者通达语言。”[21] 海德格尔通过引证格奥尔格的名为《词语》的诗来阐发他的观点:
《词语》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期待着远古女神降临
在她的深渊处发现名称——
我于是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一度幸运的漫游,我达到她的领地
带着一颗宝石,它丰富而细腻
她久久地掂量,然后向我昭示:
“如此,在深渊深处一无所有”。
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22]
海德格尔在格奥尔格的诗歌中又觅到知音。对于存在本身,对于道,是不能在语言的范围内找到正确的名称的。即使在语言的边缘和深渊,你自以为找到了像宝石那样丰富而细腻的表达方式,仍然不能恰当地描绘存在或道。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弃绝,必须打碎语言,认识到存在不是存在者,道不是物,是不能用任何词语来指称的。这时,当你在语言的破碎处看不到物的时候,你就会在语言的字里行间,顺着语言道说的方向领悟存在,领悟道,这也就是领悟语言的本质。
对于这个道理,中国语言文化中的读者不难理解。老子早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中国魏晋的玄学家王弼在《明象》篇里说:“立言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说“忘言”、“忘象”,就是告诉我们,要领悟道的深意,就不能执着于名和象,而要打破这种名指称象和象传达意的关系,就要在语言的破碎处,即在老子所说的“无”中,以观其妙。这在禅宗中,叫“自说自扫”,“过河拆桥”,“上墙抽梯”。即为说明佛理,不得不借助语言,但语言又会造成对佛理的误解,所以又要自己清扫干净,这犹如“过河拆桥”,“上墙抽梯”。我觉得苏东坡的一首诗,能巧妙地揭示这层深意:
《听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正如我们不应把琴声归于琴弦和手指一样,我们不应把存在归于存在者,把道归于物。但存在又是通过存在者展示出来的,道又是通过万事万物展示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离弃“大地”,而要在世界之中,在语言之中,领悟存在和道。诗有一种让我们进入词语又走出词语,对词语不取不舍的妙用,能帮助我们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直接领悟道,所以诗比起论述文来更有益于哲思和禅悟。南宋隐士诗人戴复古深切地洞见到这一点:
《论诗十绝》之一
欲参诗律似参禅,
妙趣不由文字传。
个里稍关心有悟,
发为言句自超然。
“诗者,天地之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对诗的论述,其基本观点与海德格尔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说中引用了荷尔德林的五个中心诗句,阐发他对诗的本质的看法。下面我想结合它们比较中国传统诗论中的相关观点。
海德格尔引证的荷尔德林论诗的第一个中心句为“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23] 这不禁使我想起孔夫子评价诗经的名言:“《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作诗是一种自由地创造它的形象世界的活动,它逸离实际的决断,不涉及现实世界中的功利问题,因此清白无邪。在中国儒家眼中,“思无邪者,诚也。”在诗经中的这些诗,无论出于怨男愁女,还是出于孝子忠臣,皆是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虚情假意。这样的诗是人的真实性情的自然表达,人的真实性情是无邪的,这些表达人的真情实意的诗歌也是无邪的。
诗最清白无邪,但也是“最危险的财富”。海德格尔所引荷尔德林论诗的第二个中心句为:“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是最危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24]这里所强调的是,语言既是创造的推动力,也是毁灭的推动力,人可以通过语言追求本真、神圣的东西,向本源回归,但也会通过语言而异化、沉沦、毁灭。中国儒家早就知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道理。诗人承担“文以载道”的职责,诗人的语言有教化作用,“修辞立其诚”,率性弘道,用诗来表达民意,申诉民怨,批评不良朝政。《诗三百》中不乏对王室政治有所讽刺、有所规劝、有所责难的作品。诗人不惧为这样的诗而付出生命代价。如果诗背离文以载道的职责,不去反映民情,不去表达人的至诚性情,转而趋炎附势,纵欲纵情,也会沦为歪诗、淫诗,成为招致亡国的“靡靡之音”。诗人驾驭语言,而人在诗的语言中看到自己的真实性情和存在之本质。
海德格尔所引荷尔德林论诗的第三个中心句为:
人已经体验许多。
自我们是一种对话,
而且能彼此倾听,
众多天神得以命名。[25]
诗言志,诗缘情,诗表达人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通过诗,不仅人与人之间得到交流,而且沟通天地人神,领悟天命和神圣的旨意。这一切都发生在诗的语言中。海德格尔写道:“我们本身所是的本真对话就存在于诸神之命名和世界之语词生成(Wort-Werden)中。”[26]我觉得这里的语词既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语词,也可以理解为“太初有道”的“道”和“与神同在”的“圣言”;而语词生存不仅是指人的造词用句,而且指“道”的生存。诗回应诸神的招呼,承担天命的责任。有关这层意思,我觉得《诗含神雾》中所引孔子话说得更好:“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诗寻求表达“天地之心”,彰显君子之德的风范,是百福的源头,是滋生万物的家园。诗把人的至诚的心与天地之心相沟通,把人的道德与天理、天命联系在一起,阐明人世间幸福的源头和万物生存的根基。因此,诗不仅表达人的生存体验,而且蕴含神圣意境。
海德格尔所引荷尔德林论诗的第四和第五个中心句分别为:
4.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27]
5.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28]
诗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通过诗的语词实现自己。诗的语词不是对现存的东西的描述,而是充满想象力的自由塑造。人的生存通过诗的词语加以开拓,放射光芒。既然是“持存的东西”,为什么能够被创造呢?按照海德格尔的解答,这里持存的东西不是指存在者,而是指存在本身。存在本身生生不息,欣欣向荣,而“诗乃是存在的语词性创建。”[29]诗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首先让万物进入敞开域的道说。诗人给尚未存在的希望中的事物构想名词,命名它们,呼唤它们产生出来。诗人开启存在本身的意义,把人类的此在牢固地建立在这种充满意义的存在的基础之上。人在大地上充满劳绩,但有了诗,人不仅饱尝劳绩中的辛苦,而且在辛苦中点燃希望。当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那么大地上的人的存在就生机蓬勃。存在本身在诗意中万古长青,永恒更新。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所说的诗人作为“神灵的传达者”和诗人开启存在本身的意义是息息相关的。诗人接受“诸神的暗示”与诗人领悟人的存在的意义是诗人的左耳和右耳,左眼和右眼。“这样,诗的本质就被嵌入到诸神之暗示和民族之音的相互追求的法则中了。诗人本身处于诸神与民族之间。诗人是被抛出在外者——被抛入那个‘之间’(Zwischen),即诸神与人类之间。但只有并且首先在这个‘之间’中才能决定,人是谁以及人把他的此在安居于何处。‘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30]由此,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的如下诗句视为诗之本质的最纯粹表现:
而我们诗人!当以裸赤的头颅,
迎承神的狂暴雷霆,
用自己的手去抓住天父的光芒,
抓住天父本身,把民众庇护
在歌中,让他们享受天国的赠礼。[31]
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视为在一个“逃遁了的诸神和正在到来的神的时代”[32]中的诗人。说得直白一些,即在一个启蒙运动之后的理性时代继续期盼神的诗人。启蒙理性动摇了以往那种对神的信仰,理性的“纯粹法则”使得这个时代的人的想象力极其贫乏,而荷尔德林依然在这个黑夜的虚无中独自坚持诗的使命。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歌听到的最强音:“存在之创建维系于诸神的暗示。”[33]这是他呼吁“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要旨。
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诗歌的特点。在中国的诗歌中具有超越精神,但这种超越是内在地超越,即:在人间的生活中,在自己的生存体验中,领悟“天道”和“天理”,从而修身养性,率性弘道,救世济民。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超越而内在,即:神创造世界,人接受上帝的启示和拯救。海德格尔的观点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所接近,他把“存在”、“道说”、“神的暗示”和人的“此在的生存”连为一体,强调天地人神的“四重奏”,于是“神的暗示”、“道说的语言”和人的生存体验的关系就被打通了。这种“四重奏”是“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前提。比较海德格尔的“四重奏”,我觉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而超越”不是落实在对神的期待中,而是落实在有道德的生活中,落实在美好的生活愿望中,落实在“鼓万物”的“生生之谓易”的盛德大业中。它反映在中国的诗魂中就是:“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我觉得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最能反映中国诗词的这种精神: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该诗词的前一段描述诗人的一种从地上到天上和从天上再到地上的思绪。人间事尽管有万般忧愁,但比起“不胜寒”的琼楼玉宇来,还是要踏实得多。人间不能克服“悲欢离合”的痛苦,但人仍然要保持一种“但愿人长久”的良好愿望和“千里共婵娟”的超越精神。
海德格尔阐发诗与思的关系是凭借现象学的方法和西方的诗歌。我想,既然现象学的方法是一种面对事情本身的方法,是一种在自己的处身情境中体认生存经验和领悟存在意义的方法,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不妨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出发,以我们自己的当下此在为基点,来阐明存在的意义。既然我们对外国的诗不得其门而入,那么我们就从中国的诗入手。在海德格尔那里透过希腊文和德文的诗歌所表现的存在意境,在中文古诗词那里以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形态深深地打动中国人的心灵,培育中国的人文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有神论的宗教观不同,但仍然体现一种超越的精神,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内在力量。海德格尔阐明存在关怀和宗教意境的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生存体验出发诠释中文古诗词中的存在关怀和人文意境,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培育道德观念的道路。
[1]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2页。
[2] 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引自《熊译海德格尔》,熊伟译,王炜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0-291页。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第240页。
[4] 熊伟借用佛教术语翻译海德格尔的哲学用语,有很多例证,如他把“Verfassung”译为“法相”,把“Seinsverfassung”译为“存在法相”。不知道佛教的法相唯识宗,可能很难理解这里“法相”的含义。
[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第227页。
[6] 转引自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5页。
[7]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7页。
[8] 同上书。第28页。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第216页。
[10]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页。
[1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页。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年,第215页。
[13] 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页。
[14]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6-157页。
[15] 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9页。
[16] 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
[17] 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页。
[18]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页。
[19]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9页。
[20]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6页。
[21] 同上书,第219页。
[22] 格奥尔格的诗,转引自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5-186页。
[23]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7页。
[24]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8页。
[25]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1页。
[26]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3页。
[27]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页。
[28]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6页。
[29]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30]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2页。
[31]引自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8页。
[32]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2页。
[33]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1页。